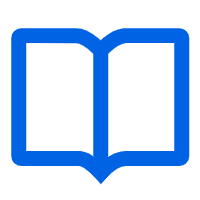电器在五行中属于什么?
古代人没有电,所以也就没有了电这种概念。《礼记·中庸》里面有“君子慎独”,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里面也有“以乡之礼教民而宾之,故曰‘宾礼’,宾礼所以亲宾也……以酒食款客,故名‘宴饮之礼’”。这里的宾和宴都是指招待客人,重点在“迎”客到家里来。
古人把需要迎到的客人分为五等——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,称为“五等宾”,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贵宾了。这些宾一般都是有身份的人,所以称“宾礼”。但不管多么有身份的人,他的身份再高也是客人,所以还是得恭恭敬敬地迎接他,这是礼仪的重点。
那么,为什么不是六等或四等呢?因为,如果多出来的那一档是私宾的话,那么对私人的礼遇就失之于滥了;反之,少了一档的话,公宾又未免显得太寒酸(比如现在一些比较土的饭店还有“四星”“三星”的招牌)!
同样道理,古代的祭祀其实也很有层次性和分寸感——“太牢”和“少牢”的设置就是考虑到猪羊牛三牲齐备过于盛大,或者只用猪牛羊中的一味就显得不够尊重。(不过今天很多餐厅在摆阔的时候喜欢用“满汉全席”这个名目,意思就是把能上的菜都上一遍,这其实是一种误会) 回到正题,由于古人在招待宾客的时候一般是把宾客带到自己家里,所以,家也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含义——引申为家庭的代称。
这一点跟现代汉语有些不同,例如我们说“家里”一般是没有人的,说“宾馆”一般也是没有房的(虽然都有例外)。但我们读古典诗词时会发现不少情况刚好相反:诗人词人在诗之中说“我家里有什么什么”或“我宾馆里有床又几间房”,这显然是不合语义的。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古典文学中的“家”和“宾馆”往往不是指具体的建筑物,而是指包括这个建筑物在内的一切,用今天的词汇就是“领域”。所以,苏轼的《赤壁赋》中有“寄居一城,求为光禄之士”,李白《襄阳歌》有“樊川李候有美名”,这都是指他们自己在襄阳住的地方(当然也有可能只是短暂的寓所)。